禪 的 修 行
撰文: 鈴木大拙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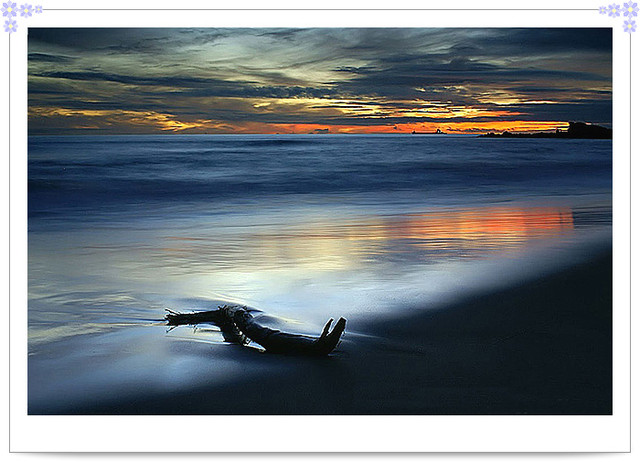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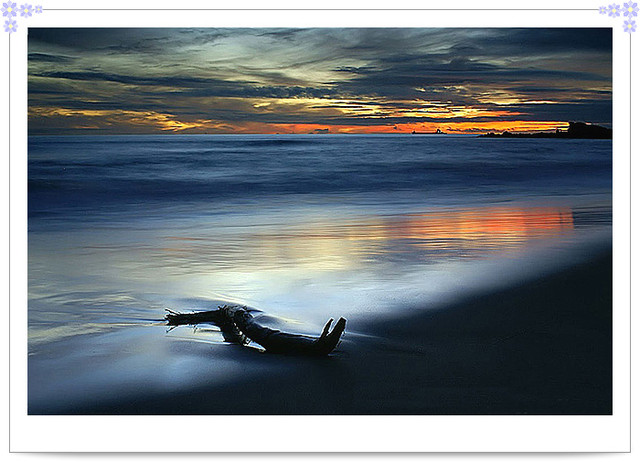
禪師們用兩種方法來訓練他們的弟子 ─
智性的方法和意志的或情意的方法。
為了發展弟子們智性的能力,
禪師們把古代所討論或形成的公案教給弟子,
讓他去思考。禪師可能要求他的弟子對諸如下列的公案表示意見:
“ 什麼是你未生之前的本來面目?”或
“ 佛法是為叫你認識本心見性成佛,但你的心在何處?”或
“ 萬法歸一,一歸何處?”或
“ 僧問趙州,如何是祖師西來意,他答道:
‘ 庭前柏樹子。’
這是什麼意思?”
弟子在接到這些問題後,會想盡辦法去解答。
他可能會想 “ 本來面目 ” 是意謂存在的最終道理,或者會想 “ 萬法歸一 ”
的一是萬物的絕對根本,而除了它自己之外,再無處可歸。
持著這些觀點,他去參見禪師,
在禪師面前展示他所有的哲學與宗教知識。
但是,這些觀點雖然可能與一般的佛教神學相合,
卻會遭到禪師的冷漠。
因為禪並不是要去證明、解釋或討論,
而是把 “ 信 ”的事實按其本來面目呈現出來。
那些習慣於將從未親身體驗的事情,而只是在口舌上搬弄的人,
那些把符號 ( 文字、觀念 ) 當實物的人,
當碰到禪師這種不妥協的反應時,才有生以來第一次發現:
他們的頭腦是多麼混淆,而他們的信仰之基礎,又是何等不穩。
如此在禪宗的訓練下,
他們會學習著清楚而明確的界定他們對事物的觀念;
他們也開始從一種完全不同的觀點來自省,
和看待外在的事物。
儘管他們不能掌握住公案的意義,這種日益得到的反省習慣
( 雖然這不是禪的主要目標 ),也會在弟子們德性與智性的訓練上,
有相當的幫助。
他可能會想 “ 本來面目 ” 是意謂存在的最終道理,或者會想 “ 萬法歸一 ”
的一是萬物的絕對根本,而除了它自己之外,再無處可歸。
持著這些觀點,他去參見禪師,
在禪師面前展示他所有的哲學與宗教知識。
但是,這些觀點雖然可能與一般的佛教神學相合,
卻會遭到禪師的冷漠。
因為禪並不是要去證明、解釋或討論,
而是把 “ 信 ”的事實按其本來面目呈現出來。
那些習慣於將從未親身體驗的事情,而只是在口舌上搬弄的人,
那些把符號 ( 文字、觀念 ) 當實物的人,
當碰到禪師這種不妥協的反應時,才有生以來第一次發現:
他們的頭腦是多麼混淆,而他們的信仰之基礎,又是何等不穩。
如此在禪宗的訓練下,
他們會學習著清楚而明確的界定他們對事物的觀念;
他們也開始從一種完全不同的觀點來自省,
和看待外在的事物。
儘管他們不能掌握住公案的意義,這種日益得到的反省習慣
( 雖然這不是禪的主要目標 ),也會在弟子們德性與智性的訓練上,
有相當的幫助。
當一個公案解決之後,另一個或許更為困難的公案,又交給了他,
以便弟子可以看出來,在所有的公案中,都普遍存在著一個原理;
這種訓練可以依照弟子的願望,無限制的做下去。
以便弟子可以看出來,在所有的公案中,都普遍存在著一個原理;
這種訓練可以依照弟子的願望,無限制的做下去。
禪宗關於意志或情意方面的訓練,是用坐禪方式的來實行。
弟子在一個規定的時間靜坐,思考禪師所交給他的公案。
坐禪可由弟子獨自實行,也可在專門為此而設的禪堂與大家一同實行。
弟子在一個規定的時間靜坐,思考禪師所交給他的公案。
坐禪可由弟子獨自實行,也可在專門為此而設的禪堂與大家一同實行。
坐禪的意思不是要造成一種自我催眠狀態。
它的目的在使心靈得到恰當的平衡,
並把注意力依照自己所願意的方向集中。
大部份人,特別是在工商社會的今日,如此易於興奮、衝動,
以致常常過早的耗盡了他們的精力,最後終致喪失心靈的平衡。
禪一方面要挽救精力這種無益的浪費,
一方面可以說是儲蓄心力。
它的目的在使心靈得到恰當的平衡,
並把注意力依照自己所願意的方向集中。
大部份人,特別是在工商社會的今日,如此易於興奮、衝動,
以致常常過早的耗盡了他們的精力,最後終致喪失心靈的平衡。
禪一方面要挽救精力這種無益的浪費,
一方面可以說是儲蓄心力。
何謂禪那?禪那在梵文本來的意義是平和、平衡或平靜,
但就宗教上來說,它更具備著自省或內省的意義。
這並不必然是對深刻的形而上學問題做沉思,
也不是去思索某個神祗的德性,也不是思念世俗生活的短暫。
它在佛教中的意義,簡單而概略的說,
是一種時時從世俗事物的煩擾站開,
把某些時間貢獻於自省自心的習慣。
當這個習慣徹底建立之後,
就可以保持心智的澄清與心情的愉悅,
即使在日常生活的旋渦中亦復如是。
因此,禪那是一種平靜訓練,
旨在使心靈有沉靜的時間,免得放野;
它把虛幻而卑俗的心意導向真切與誠實;
它使我們對於超越感官的事物感到興趣;
它在我們心中尋見一種精神力的存在,
可以溝通有限與無限之間的鴻溝;
最後它會就我們脫離無明的枷鎖與痛苦,
安全的將我們導致涅盤的彼岸。
但就宗教上來說,它更具備著自省或內省的意義。
這並不必然是對深刻的形而上學問題做沉思,
也不是去思索某個神祗的德性,也不是思念世俗生活的短暫。
它在佛教中的意義,簡單而概略的說,
是一種時時從世俗事物的煩擾站開,
把某些時間貢獻於自省自心的習慣。
當這個習慣徹底建立之後,
就可以保持心智的澄清與心情的愉悅,
即使在日常生活的旋渦中亦復如是。
因此,禪那是一種平靜訓練,
旨在使心靈有沉靜的時間,免得放野;
它把虛幻而卑俗的心意導向真切與誠實;
它使我們對於超越感官的事物感到興趣;
它在我們心中尋見一種精神力的存在,
可以溝通有限與無限之間的鴻溝;
最後它會就我們脫離無明的枷鎖與痛苦,
安全的將我們導致涅盤的彼岸。
禪那有時可以做為Samatha或samadhi和samapatti的同義詞。
Samatha意謂寂靜,事實上和禪那同義,後者較為被常用。
Samapatti本義為‘ 擺平 ’或‘ 平衡 ’,在佛教中則謂意識的平衡,
在其中既不起驚醒,又不起漠然,而是心靈安靜的集中於所思。
Samadhi意指自動的或非自動的完全凝集在所觀想的對象中。
當一個人的心同萬物最終之理合而為一,
並且除了這合一之外不再有其他意識時,
就說處於一種三昧狀態。就此而言,禪那是達到三昧的方法或歷程。
如此說,禪那的訓練益處不止一種,它不僅使吾人在實際生活中獲益,
在德性與精神上亦複如是。沒有人會否認沈著,節制脾氣,控制情感,
以及主宰自己所帶來的極大益處。在激動之際感情有時會如此猛烈,
以致會將自己徹底毀滅,但一個頭腦冷靜的人,
卻知道如何給心靈以必要的休息與沉靜時刻,免得投入情感的旋渦之中。
而頭腦的冷靜,雖然有一部份是來自天生,卻可以由禪那的訓練而獲得。
從智性上來說,禪那可以保持頭腦的清楚與明澈,而在任何必要的時刻,
可以把心意集中在當前的問題上。推理的精確甚有賴於心靈不受情緒的影響,
而科學的觀察必賴觀察者的持續有定。不論一個人心智的發展是何種狀態,
訓練自己養成平靜的習慣,必然有得無失。
在工商文明的今日,大部份人甚少有時間接觸精神文化。
他們可以說根本不知道還有永久價值的事物存在,
他們的心如此糾纏於日常生活的瑣屑中,
以致他們覺得要,免除這些事物不斷的干擾,其實是極端困難的。
即使每天從他們一成不變的工作回家之後,他們還有許許多多
讓他們興奮的事物去做,以致他們本已虛耗的神經系統消耗殆盡。
如果他們不早死,必也精神盡衰。
他們似乎從不知道安息的福祉。
他們似乎沒有能力過內在的生活,並在此中發現永恆的愉悅之源。
生命對他們不過是一個沉重的負擔,而他們的任務就是背負這個重擔。
因此,禪那的福音,設若他們能真心誠意去行,必將成為他們天國般的至福。
從生理學意義上來說,禪那是精力的儲蓄;
它像是一種精神蓄電池,將大量的精力藏在其中,
而這個蓄電池在任何需用的時候就放出巨大的能量。
一個受過禪那訓練的心靈從不浪費它的精力,造成無益的虛耗。
從表面上去看,它可能是沉悶的,無趣的,好像半醒半睡似的,
但當實際需要,它卻會完成奇跡;一般耽於浪費的人,
遇到強烈的衝動或刺激,稍做掙扎就完全癱瘓,
因而立即投降,因為他沒有精力的儲藏。
這是東方心智與西方心智許多典型的不同之一。
東方文化的每一部門都強調精力的儲存,要將精神力量的泉源保持充實滋潤。
東方人訓練他們的青年,要把心智內含,不要無意義的顯露本領、知識及德性。
他們會說,只有淺水才有聲音,深的漩渦卻無聲無息。
而西方人,就我的瞭解所見,卻喜歡像孩子般坦誠的把他們一切所有展示出來;
他們喜歡熱烈的,不遺餘力的生活,而這種生活不久就乾涸了他們所有的精力。
他們似乎不會儲存任何東西以待閒暇之用。他們確實有坦誠而開放的特點,
這些有時似乎是東方所缺的;但西方人顯然缺乏東方人的深度,
後者似乎從不熱切、浮躁與不可抑制。
老子的教訓或 Bhagavadgita的教訓,確實是西方人所不易接受的。
當然,西方人也有例外,這同東方人相似。不過一般來說,西方是活力的,
而東方則是神秘的;因為東方人的理想乃是如絕對者一般不可解、
不可測、不可思議。禪那的實踐可以說是到達這個理想的方法之一。
禪那的實踐常被人混同為催眠或自我催眠,這是我在此處要加以駁斥的。
這兩者的不同,是任何具有清晰心靈的人都可以看出的,
因為催眠是意識的一種病理性擾亂狀態,而禪那卻是意識的完美正常狀態。
催眠是一種自我幻覺,是全然主觀的,不能從客觀上去證實;
但禪那卻是一切心智力量保持平衡的意識狀態,在這種狀態下,
沒有任何思想或功能,是壓制其他思想或功能的。
禪那如同在激蕩的水面上澆油,以平和激蕩一般。
在一片廣大鏡面上,沒有波濤起伏,沒有泡沫翻動,沒有浪花激起。
就是在這完美的意識之鏡上,億萬反影來去而不打擾它一絲澄澈。
在催眠狀態下,則是某些心智與生理器官片面,而其他部份完全停頓,
因此整個的意識系統陷於錯亂;而結果是喪失了有機體的平衡,
這正與禪那的實踐所得的結果完全相反。
另有一些膚淺的批評家,認為佛教的禪那,
是對於某種高度抽象的思想之聚精會神的沉思,
而這種集中其作用有些像自我催眠,
能夠將心靈導致一種稱之為涅盤的恍惚狀態。
他們之所以有如此嚴重的錯誤看法,
是由於他們從未瞭解宗教意識的本質,
因為佛教的禪那同抽象和自我催眠根本無關。
禪那所要完成的,是叫我們去實現寓含在我們心靈內的宇宙之道。
禪那要我們去認識最具體的生命,因之也是最有普遍意義的生命。
乾燥無趣又沒有生命的抽象問題是哲學家們的題材。
佛門弟子所關心的不是這類事情。
他們要求直接看到事實本身,
而不是以哲學的抽象為媒介。
全站熱搜


 留言列表
留言列表

 {{ article.title }}
{{ article.title }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