直 觀 與 般 若
【禪學隨筆】 鈴木大拙 著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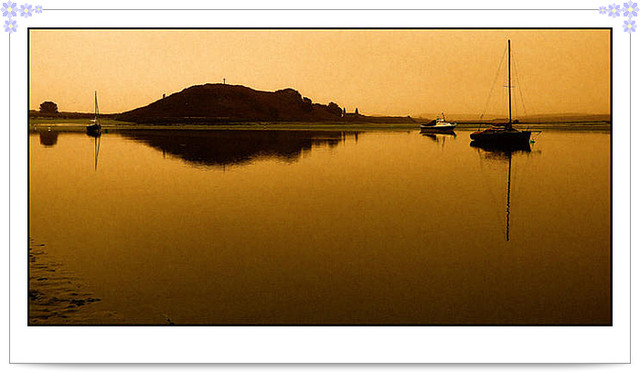
唐代的京兆興善寺的惟寬禪師,
有一次被一個和尚問道:“狗有沒有佛性?”
他答道:“有。”
和尚又問:“你有沒有佛性?” “我沒有。”
“為什麼一切眾生都有佛性,你卻沒有佛性呢?”
“因為我不是你所說到的 ‘眾生’。”
“如果你不是眾生,你是佛嗎?”“也不是。”
“那麼你究竟是什麼?” “我不是一個‘什麼’。”
和尚最後說:“那是我們能夠看到或想到嗎?”
禪師回答:“那是不可思不可議的。因此稱之為不可思議。”
另一次有人問他:“什麼是道?”
禪師回答:“就在你前面。”“為什麼我看不到?”
禪師說:“因為你有一個‘我’,所有你看不到。
只要仍舊有你和我,就有著相互的限制,
就不可能有真‘見’。” “設若如此,
如果既沒有‘你’也沒有‘我’,還能有‘見’嗎?”
禪師答道:
“如果既沒有‘你’,也沒有‘我’,
還有誰要見呢?”
如此我們可以看出來,般若直觀是一個完全獨立特異的直觀,
而不能夠歸類於其他任何我們所瞭解的直觀中。
當我們看到一朵花,我們說那是一朵花,而這是一件直觀行為,
因為知覺也是一種直觀。但是當般若觀照一朵花時,
它不但要我們觀照一花朵,同時還要觀照不是花的東西。
換句話說,在花尚未成花以前,看到這朵花 ── 而這樣做,
並不是由於思想上的假設,而是“直接”見到。
用更為形而上學的方式來說,般若會這樣問我們:
“在世界未創生以前,神在何處?”或者以個人為物件來問:
“當你死後,焚化成灰,散在空中,你的自我在何處?”
對於這些問題,般若要求“直下”回答,
而不准片刻的反省或推論。
哲學家們當然想用他們所專長的某種邏輯方式,
來解決這些問題,並且可能宣佈這些問題是荒謬的,
因為它們不合於智性推理。或者他們會說要寫一本書,
來提出可解的答案(設若有此答案)。
但是般若的方法卻完全不同,
如果提出的要求,是要看到花開以前的花,
般若毫不猶豫的會說:“多麼美麗的一朵花呀!”
如果是關於世界未創生以前的神,般若就會抓住你的脖子,
猛力搖撼,說:“多麼沒用的一段幹屎橛子!”
如果是關於你焚化成灰以後在何處,般若禪師會大聲叫你的名字,
你回答說:“在這裏,什麼事?”他會說:“你在哪裡?”
般若直觀當下解決這類嚴重的問題,而哲學家或思辨家卻花費許多時辰,
或許多年,來尋求“客觀證據”,或“實驗證明”。
而不能夠歸類於其他任何我們所瞭解的直觀中。
當我們看到一朵花,我們說那是一朵花,而這是一件直觀行為,
因為知覺也是一種直觀。但是當般若觀照一朵花時,
它不但要我們觀照一花朵,同時還要觀照不是花的東西。
換句話說,在花尚未成花以前,看到這朵花 ── 而這樣做,
並不是由於思想上的假設,而是“直接”見到。
用更為形而上學的方式來說,般若會這樣問我們:
“在世界未創生以前,神在何處?”或者以個人為物件來問:
“當你死後,焚化成灰,散在空中,你的自我在何處?”
對於這些問題,般若要求“直下”回答,
而不准片刻的反省或推論。
哲學家們當然想用他們所專長的某種邏輯方式,
來解決這些問題,並且可能宣佈這些問題是荒謬的,
因為它們不合於智性推理。或者他們會說要寫一本書,
來提出可解的答案(設若有此答案)。
但是般若的方法卻完全不同,
如果提出的要求,是要看到花開以前的花,
般若毫不猶豫的會說:“多麼美麗的一朵花呀!”
如果是關於世界未創生以前的神,般若就會抓住你的脖子,
猛力搖撼,說:“多麼沒用的一段幹屎橛子!”
如果是關於你焚化成灰以後在何處,般若禪師會大聲叫你的名字,
你回答說:“在這裏,什麼事?”他會說:“你在哪裡?”
般若直觀當下解決這類嚴重的問題,而哲學家或思辨家卻花費許多時辰,
或許多年,來尋求“客觀證據”,或“實驗證明”。
這是因為般若的方法,與分別識的方法,或智性方法相對。
由於這個原因,般若所說的話,從分別識看來總是如此荒謬、
如此莫明其妙,甚至不加思索,便會把它拋棄。
分別識是分別原理與概念化原理,
並因之是處理日常生活最有效的武器。
由於這個原因,我們往往把它認做最根本的方法,
以面對相對世界;但是卻忘記了這個世界
是另外一個東西的產物,這種東西比智性遠為深沉;
事實上,智性的存在以及它八面玲瓏的用途,
都是得自這個神秘物。
分別識的這種推論方法是悲劇性的,
因為它使我們的心與精神,產生不可言說的痛苦,
使得生活成為不幸的重擔;但我們不可忘記,
就是由於這個悲劇,我們才覺醒到般若的存在。
因此,在表面上,般若對分別識雖然似乎粗厲,
實則對它總是寬容的。般若對它粗厲,是為了提醒它,
讓它瞭解它的本位,因而同般若和諧工作,
以便給予心和腦,自從人類意識覺醒以來,就在尋求的東西。
因此,當般若粗暴的摧毀一切推理的規律之際,
我們必須瞭解,這是給予智性一個訊號,
讓它瞭解到一個十分嚴重的危機。當分別識看到這個訊號,
它就應當悉心諦聽,然後徹底審查自己。
它切不可再繼續采行“合理化藉口”之途。
分別識的基礎是般若,是般若使得分別識以分別原理而運作,
這是不難識別出來的,因為若沒有某種東西行合一作用,
分別作用就是不可能的。
除非有某種東西存在於主體與客體之下,做它們的基礎,
但又既不是主體亦不是客體,則主體與客體之分就是不可能的。
這個基礎乃是主體與客體,可以在其中運展的場所,
是使得主體可同客體分離,而客體可同主體分離之處。
如果這兩者沒有任何關連,
則我們甚至不能說,它們是分離的或對立的。
在主體中必有客體的成份,在客體中必有主體的成份,
這乃是使得兩者之分別,與關連成其為可能之處。
再者,由於這個最基本的原理,不能夠從智性的分化作用去探討,
因此必須由另外的方法去達到它。它是如此徹底的根本之物,
因此一切分別性的工具都無法置喙,我們必須訴之於般若直觀。
當我們說般若存在分別識之基本,或般若透入分別識時,
我們可能會以為,有著一種特別的部門,稱之為般若,
它行著一切穿透分別識的工作。
這種想法是把般若當做了分別識來看待。
般若並不是一般判斷原理,使主體由此同客體相關。
般若超乎一切判斷,而是不可表敘的。
關於般若,我們所常用的另一個錯誤想法,
是以為它傾向於泛神論。因之在學者之間就把佛教哲學
列在泛神論之中。這是一個不正確的觀點,
因為般若不屬於分別識的範疇,
因此凡是從分別識所引生出來的判斷一概不能用之於般若。
在泛神論之中,仍有主體與客體之分,
而萬象世界中有一個無所不透的神 ── 這個觀念
仍舊是由智性的假設而產生的看法。
般若直觀截斷這一層。在般若直觀中沒有一與多之分,
沒有全體與部份之分。
一葉草抬起,整個宇宙在其中展現;
在每一個毛孔中跳動著,
展現過去、現在、未來三界的生命。
而這是由般若直接直觀到的,並非由推理的方法推論到的。
般若的特色即是這種“直接”。
如果我們在此處用推理,那就太遲了:
如禪師所說:“遠如萬里白雲般”。
由於這個原因,般若所說的話,從分別識看來總是如此荒謬、
如此莫明其妙,甚至不加思索,便會把它拋棄。
分別識是分別原理與概念化原理,
並因之是處理日常生活最有效的武器。
由於這個原因,我們往往把它認做最根本的方法,
以面對相對世界;但是卻忘記了這個世界
是另外一個東西的產物,這種東西比智性遠為深沉;
事實上,智性的存在以及它八面玲瓏的用途,
都是得自這個神秘物。
分別識的這種推論方法是悲劇性的,
因為它使我們的心與精神,產生不可言說的痛苦,
使得生活成為不幸的重擔;但我們不可忘記,
就是由於這個悲劇,我們才覺醒到般若的存在。
因此,在表面上,般若對分別識雖然似乎粗厲,
實則對它總是寬容的。般若對它粗厲,是為了提醒它,
讓它瞭解它的本位,因而同般若和諧工作,
以便給予心和腦,自從人類意識覺醒以來,就在尋求的東西。
因此,當般若粗暴的摧毀一切推理的規律之際,
我們必須瞭解,這是給予智性一個訊號,
讓它瞭解到一個十分嚴重的危機。當分別識看到這個訊號,
它就應當悉心諦聽,然後徹底審查自己。
它切不可再繼續采行“合理化藉口”之途。
分別識的基礎是般若,是般若使得分別識以分別原理而運作,
這是不難識別出來的,因為若沒有某種東西行合一作用,
分別作用就是不可能的。
除非有某種東西存在於主體與客體之下,做它們的基礎,
但又既不是主體亦不是客體,則主體與客體之分就是不可能的。
這個基礎乃是主體與客體,可以在其中運展的場所,
是使得主體可同客體分離,而客體可同主體分離之處。
如果這兩者沒有任何關連,
則我們甚至不能說,它們是分離的或對立的。
在主體中必有客體的成份,在客體中必有主體的成份,
這乃是使得兩者之分別,與關連成其為可能之處。
再者,由於這個最基本的原理,不能夠從智性的分化作用去探討,
因此必須由另外的方法去達到它。它是如此徹底的根本之物,
因此一切分別性的工具都無法置喙,我們必須訴之於般若直觀。
當我們說般若存在分別識之基本,或般若透入分別識時,
我們可能會以為,有著一種特別的部門,稱之為般若,
它行著一切穿透分別識的工作。
這種想法是把般若當做了分別識來看待。
般若並不是一般判斷原理,使主體由此同客體相關。
般若超乎一切判斷,而是不可表敘的。
關於般若,我們所常用的另一個錯誤想法,
是以為它傾向於泛神論。因之在學者之間就把佛教哲學
列在泛神論之中。這是一個不正確的觀點,
因為般若不屬於分別識的範疇,
因此凡是從分別識所引生出來的判斷一概不能用之於般若。
在泛神論之中,仍有主體與客體之分,
而萬象世界中有一個無所不透的神 ── 這個觀念
仍舊是由智性的假設而產生的看法。
般若直觀截斷這一層。在般若直觀中沒有一與多之分,
沒有全體與部份之分。
一葉草抬起,整個宇宙在其中展現;
在每一個毛孔中跳動著,
展現過去、現在、未來三界的生命。
而這是由般若直接直觀到的,並非由推理的方法推論到的。
般若的特色即是這種“直接”。
如果我們在此處用推理,那就太遲了:
如禪師所說:“遠如萬里白雲般”。
因此,令人困惑不解的言詞成了般若直觀的特色。
由於它超越了分別識與邏輯,它就並不在乎同自己相矛盾;
它知道矛盾乃是分別識的產物,而分別作用是分別識使然。
般若否定原先肯定的,又肯定原先否定的;
它對於這個二元世界有其自己的處理方法。
花是紅的,又不是紅的;橋在流而不是水在流;
木馬嘶,石女舞。
說得更為理論一些,般若直觀既能如此,
則一切與分別識相關的,也就同樣屬於般若;
般若是整體在那裏的。
即使當它顯露在由分別識所做的每個肯定與否定中時,
它都是整體不分的。分別識之為分別識,
就在其將自身偏於極端,但般若卻從不喪失它的整體性。
對於般若直觀的本性,佛教徒所愛用的比喻,
是把它比之于映現在清潔程度差異極大的各種水中的月亮,
從一滴水到廣大的大海都有月亮映現。
然而,這一個比喻也很容易受人誤會。
由於月影雖無限可分,月亮卻是一個,
所有般若直觀可能被人認為是由“多”抽象而得的“一”。
但用這種方式來談般若直觀是毀了它。
它的一或整體或自足,若必須對我們的分別心來做解釋,
說到最後仍舊無法做合理或數學式的解釋。
但由於我們的心總是要求著解釋,我們可以這樣說:
它並非多中的一,
也不是一中的多;
而是一即多,多即一。
換句話說,般若即分別識,
而分別識即般若 ─
但這是由 “ 直觀 ” 而得,
並非得自冗長的、
吃力的與複雜的思辨過程。
由於它超越了分別識與邏輯,它就並不在乎同自己相矛盾;
它知道矛盾乃是分別識的產物,而分別作用是分別識使然。
般若否定原先肯定的,又肯定原先否定的;
它對於這個二元世界有其自己的處理方法。
花是紅的,又不是紅的;橋在流而不是水在流;
木馬嘶,石女舞。
說得更為理論一些,般若直觀既能如此,
則一切與分別識相關的,也就同樣屬於般若;
般若是整體在那裏的。
即使當它顯露在由分別識所做的每個肯定與否定中時,
它都是整體不分的。分別識之為分別識,
就在其將自身偏於極端,但般若卻從不喪失它的整體性。
對於般若直觀的本性,佛教徒所愛用的比喻,
是把它比之于映現在清潔程度差異極大的各種水中的月亮,
從一滴水到廣大的大海都有月亮映現。
然而,這一個比喻也很容易受人誤會。
由於月影雖無限可分,月亮卻是一個,
所有般若直觀可能被人認為是由“多”抽象而得的“一”。
但用這種方式來談般若直觀是毀了它。
它的一或整體或自足,若必須對我們的分別心來做解釋,
說到最後仍舊無法做合理或數學式的解釋。
但由於我們的心總是要求著解釋,我們可以這樣說:
它並非多中的一,
也不是一中的多;
而是一即多,多即一。
換句話說,般若即分別識,
而分別識即般若 ─
但這是由 “ 直觀 ” 而得,
並非得自冗長的、
吃力的與複雜的思辨過程。
全站熱搜


 留言列表
留言列表

 {{ article.title }}
{{ article.title }}